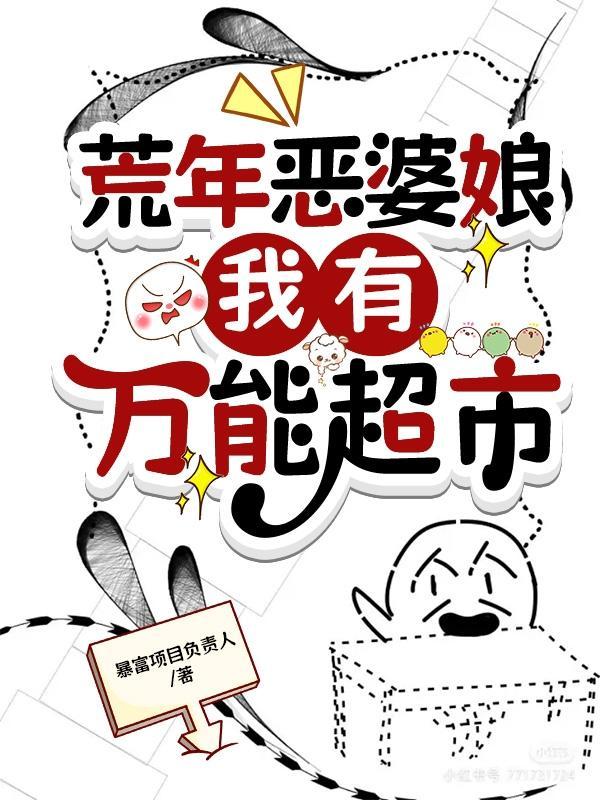九曲小说>[HP]蝴蝶效应 > 98承诺(第2页)
98承诺(第2页)
是他在定时朝你家里寄钱,也许他会知道。”
“食死徒。”奥罗拉用手指转了转面前的杯子,“你是说,对我用黑魔法的那个人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所以才想杀了我是吧”
贝芙莉点头,“只可能是这样。我和雷古勒斯通过几次信,也提到过你父亲。他对你父亲也有印象,是当时凤凰社里挺有名的人,我想那个人”她皱了皱眉,似乎对于提到黑魔王感觉很不舒服,接着说,“一定想过要杀掉你父亲和他的家人。”
“我想过。”奥罗拉低头,纯白的热气升腾进她眼里,晕开一片模糊,“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仅仅我自己没有印象,连沃克斯也没有。”
这确实让人很费解。
“有一个猜想。”比尔说,蓝眼睛在沃克斯和奥罗拉身上来回流转了一圈,“也许沃克斯本来也是知道的,只不过和你一样被抹去了记忆。如果对方打定主意不想让奥罗拉你记得这件事,那他会因为沃克斯和你的关系而抹掉他的记忆就一点也不让人奇怪了。”
奥罗拉沉默了很久,最后起身,抿着嘴唇微笑了下:“谢谢你们,我得去找一下斯内普教授了,蓝莓酱和葡萄酥它们肯定饿坏了。要不我们改天见”
“嗯。改天见。”
出门的前一秒,沃克斯突然喊住了奥罗拉:“你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会陪着你的,对吧”
奥罗拉呆了一下,拉着门环的手逐渐滑落下来。
然后她走回去,用力拥抱了他们三个:“我会适应好的。”
说完,她和朋友们道别离开了。走之前,她还听到比尔突然开口说:
“要不,我们来讨论下刚刚预言考试的问题”
“闭嘴”
敲门声响起了,挺有标志性的力度和节奏。
斯内普头也没抬,仍旧在忙碌于批改面前的大堆论文,左手举起魔杖将窗户隔空打开,说:“进来。”
奥罗拉推开门,在门口迟疑了一会儿,因为外面天气一直阴沉昏暗着的缘故,地窖办公室里的光线条件即使开着窗也并不好,刚进来的时候,视线里完全是盲的。她下意识地低头,用脚尖去试探面前的楼梯。
刚踩到第一级,门口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黄铜色调的火光一下子挤走了门口盘踞的黑暗,奥罗拉抬头看着斯内普,对方放下魔杖,依旧没什么其他动作。
“教授您好,打扰了。”奥罗拉说着,把魔法挎包取下来放在地上,打开的时候,上面的魔法部标记照例闪了一下。
她很快顺着里面的楼梯进到挎包里,刚提着装满肉类的铅桶打开门,蓝莓酱就吱吱乱叫着撞进奥罗拉的怀里,亲昵地蹭着姑娘的脖颈。
奥罗拉摸着它的头,把手里的食物分散出去。巴克比克和鸟蛇葡萄酥有些不高兴,因为奥罗拉好几天没下来看它们了,怎么哄都不肯吃东西,还老是瞪着眼睛凶过来。
奥罗拉很耐心地安抚着这两只闹别扭的魔法生物,一遍一遍地抚摸着它们的羽毛和身躯。她看着它们,像是要把它们印在脑子里那样,她很怕自己在将来看不见以后,会记不得它们的样子。
吃饱了的咖啡豆乖巧地走过来亲亲奥罗拉的头,它现在已经是完全成年的体型了,翼展宽大,身形优美流畅,皮肤漆黑得像夜空那样。
驯兽者的情绪和魔法生物的情绪是相互影响的,奥罗拉很快就现葡萄酥它们都变得恹恹的,很没精神的样子。蓝莓酱连动物脑髓都不吃了,趴在奥罗拉的肩膀上耸拉着头。
“你们别不开心了。”奥罗拉拿起切好的雪貂肉块递给巴克比克,“我这次多待一会儿好不好。”
于是她一个下午什么都没干,就在这里和她的魔法生物们一起,待到斯内普开始敲挎包提醒奥罗拉该出来了为止。
她基本可以想象出来自己爬出挎包的时候,面前的魔药教授是一副什么阴沉的表情。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当她真的看到对方的时候,斯内普只是微微拧着眉头有些不悦地看着她,重新坐回椅子上,说:“我几乎要以为你在你的挎包里迷路了,菲尔德小姐。你这次下去的时间有点太长了,你不觉得吗”
奥罗拉把挎包收拾好:“不好意思教授,我只是想想多看看它们。”斯内普听明白了她的意思,略微顿了顿后,冷淡地睨着她,语气缓慢到近乎刻意:“你有的时间来看它们。”
这句话让奥罗拉战栗了一下,她茫然地看着阴影交
叠挤压的办公室,声音低垂零落:“不会的,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斯内普的笔尖轨迹断裂了,拖凝出多余的细微划痕。他抬头看着面前的少女,脸孔公式化成面具那样僵冷,找不到一丝的柔软和人气,眉间的皱痕更深刻了。
一种强烈的冲动迫使奥罗拉正对上对方漆黑冰凉的眼睛,让她来不及去细想自己在干什么,以及这么做合不合适和有什么后果。她只是很想朝面前这个人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那些她拼命写信也不敢透露的,和朋友交流也无法开口的,每天每夜折磨着她的压抑和恐惧。
她只想告诉自己的这位教授。
“我想要看清楚那些远处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教授。很困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奥罗拉说着,眼睛在环境里仅有的碎光下折射着清亮的光,身体有些无法控制地微微颤抖着。她站在这一片昏暗的地窖办公室里,像朵被黑暗重压逼仄到无路可逃的火花,抖动着闪烁着,随时都会熄灭那样,鲜艳而脆弱。
“我一开始以为我只是普通的雪盲症,就像您知道的,赫奇帕奇家族的遗传病。可是后来去了圣芒戈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眼睛被一种能致死的黑魔法割伤过,我早就该瞎了才对。”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斯内普放下了笔,手顺势滑下去搭在靠背椅扶手的软垫上,指骨凛硬。奥罗拉摸不准他是不是在考虑怎么把自己轰出去,但是她不想停。她有种预感,如果自己现在不说,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可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了,一点印象都没有,沃克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他也不记得有这种事生过。就好像我的某一个噩梦成真了一样,只是它生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看到,但留下的伤痕是真的。”
“我的记忆被人修改过删除过,不是完整的,也不是最真实的。就像我一直都以为我只是个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的人。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其实是个巫师,而且是赫奇帕奇家族的后裔。”
“我从来都不是我以为的样子。我甚至不知道我记忆里有多少是真的值得我去相信的,我到底还忘记了些什么,它们对我
是否重要。”
“我不害怕未知,教授。但是我害怕我一直依赖和深信不疑的东西都是假的。还害怕我会再也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