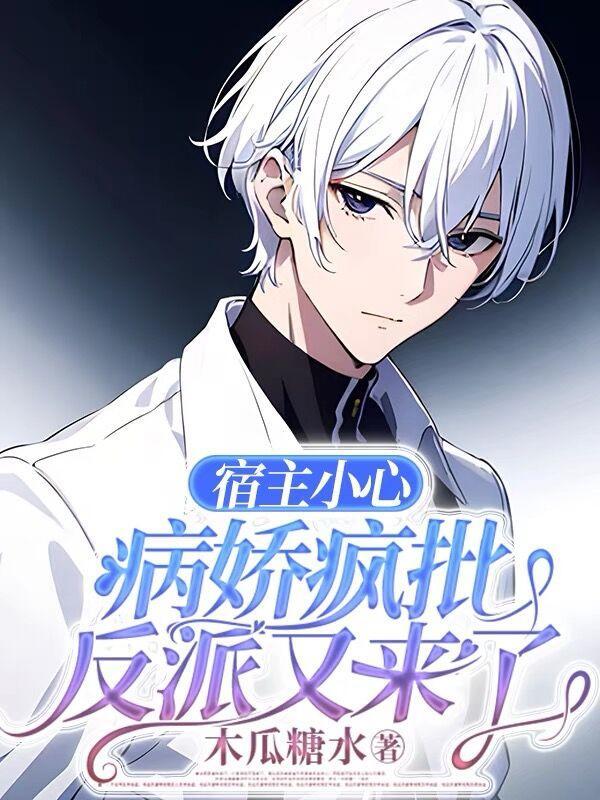九曲小说>快穿:绿茶女配她身娇体软 > 第48章 炮灰长公主她拿了白月光剧本48(第1页)
第48章 炮灰长公主她拿了白月光剧本48(第1页)
裙下废臣。
她将这几个字咬的很重,故而他也听的很清楚。
这算什么?
他不是没想过她欺瞒他,为了去辨别那一颗心到底是真是假,他昨夜仍在试探她。
看到她满眼真情实意,是他怕了,是他往后退了一步,在大理寺牢狱之中对她百般羞辱,辜负了那一片真心。
可是他怕,怕那汹涌如潮的爱意将他淹没,让他忘了肩上背负的血海深仇,忘了谭家几百条性命被那一道圣旨,一把大火焚烧殆尽的景象。
那些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哀嚎与求饶声,十多年来夜夜回荡在他耳边,他怎敢忘记,又怎能忘记。
他执意要与她一刀两断,也下定决心要为谭家复仇,哪怕
哪怕最后她死于他的刀下,他也会在她死后挥刀自戕,来生无仇无恨,他愿护她一辈子,山海不移。
可她身边的小丫鬟却与他说
为了救他,她一路从龙涎殿跪到大理寺,不顾市井上的百姓冷嘲热讽,不管朝堂大臣戏谑讥嘲。
她担心他手臂上的伤,还担心他在牢里吃不好,带了药,带了亲手做的糕点来瞧他。
而他对她恶语相向,将她公主的矜贵践踏了个粉碎。
一想到那些话,檀迟西觉得外头人人骂他“畜生”还是怜惜他了。
他千算万算,将这天下,将所有人玩弄股掌之间,唯独啊他低估了他对她的情爱,他终于还是心甘情愿成为她的手中刀,裙下臣。
血海深仇在身又如何,他愿负天下人,也不愿再负她。
可是
他在这冬雪里不知站了多久,等了多久,到头来等到她的一句“裙下废臣”。
这漫天落雪削疼了他握伞的手,也冻僵了他的双足,而那句“裙下之臣”仿佛剥掉了他的衣裳,让那落雪如刀剑,片片剜心刻骨。
“檀迟西,本宫虽不知道你是如何从大理寺逃出来的,但陛下已经罢了你的官职,你那些旧部也纷纷倒戈右相。念在你与本宫有旧,本宫只当今夜没瞧见你,放你一条生路。”
马车帘子放下,车夫扬手准备挥鞭驾马,檀迟西将手中伞掷去,伞柄重重插入厚雪之中,挡住了马车去路。
他死死望着那垂下的帘子,雪落进眼里,他也不揉,任其与眼底的温热融在一起。
“废臣檀迟西,多谢公主不杀之恩。”他哽声轻笑,似讥似嘲,“公主如此演技,不去戏班开嗓颇为可惜。”
“昔日掌印权势滔天,本宫也只能委身于下,若是掌印还是从前那个掌印,您喜欢什么样,本宫就能变成什么样。可惜啊,掌印已是丧家之犬,将死之人,本宫又如何敢把自己托付给你?”
“所以,公主便选了新的入幕之宾?”
“檀迟西,本宫要的是这天下,谁能把这天下拱手送给本宫,本宫自当选谁成为裙下臣。”
“好!好啊——”他肆无忌惮的放声大笑,也在掩饰满身的大悲,“废臣恭送公主,亦祝公主得偿所愿!”
马车驶进宫门,愈行愈远,而车内的少女正用双手死死捂着唇,生怕这痛哭声传入还站在雪地里那男人的耳中。
又滚又烫的泪珠打湿她的手背,蜷缩在一起的身子不停颤,像是忍着什么疼,不敢说,只能拼了命的竭力去忍。
霍雍替她整好衣裳,大掌轻落在她头顶慢慢拍抚,“霍雍僭越,但殿下也不必忍了,他听不到。”
“霍哥哥——”少女扑进男人怀中,双手紧攥着他的衣衫,埋在那坚实的胸口泣不成声。
霍雍叹了口气,将人揽紧。
他眼睫压下心疼,问道,“殿下既然心悦他,何必如此?”
“若他是谭家郎,我二人便是有着血海深仇。若他不是幼梨时日无多,何须耽误他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