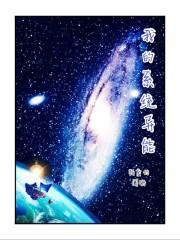九曲小说>快穿:病美人仙君又拿白月光剧本 > 第47章 朝堂白月光帝师47(第2页)
第47章 朝堂白月光帝师47(第2页)
云子猗原本正在写方子,闻言手一顿,在纸上留了好大个墨点:“你怎么比他还离谱。”
“那唤夫君也成。”卫彰说这话时嬉皮笑脸的,瞧着确实只像一句玩笑。
可云子猗听到了他的心声。
【还真是做梦都想听先生唤我一句夫君啊。】
便没法再将刚才所说的种种,皆当成玩笑话。
大约是经历过祁尧的事,云子猗很快猜到了卫彰的心思。
卫彰或许对他……也有些出师生之谊的喜欢。
甚至这样一想,从前的许多事都说得通了。
“先生怎么了?”卫彰见云子猗的脸色沉了下来,以为是自己的玩笑开过了头,忙解释道,“我只是玩笑,随便说说的,先生若不喜欢,我再不这么说便是了。”
“无事。”云子猗平复了一下心绪,换了张纸,重新写那方子,落笔前,想了想还是又添了一句,“这种话以后还是不要说了。”
卫彰抿了抿唇,心头一阵莫名的慌乱,却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乖乖点点头,不敢吭声。
祁煦也不解于云子猗突然变幻的态度,思来想去,想到一个可能。
【不会是先生在宫里那段日子,床笫间被祁尧逼着叫过夫君吧?】
云子猗刚写了两个字的药方,又换了一张新纸。
——
半年了。
祁尧支走了所有宫人,坐在床榻边,神色怔忡。
半年了,他派了那样多的人出去,依旧没有寻到先生半点儿音讯,大齐万里江山,要寻一个人堪比大海捞针,若是先生存心躲着不愿再见他,他是不是真的穷尽一生都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那简直还不如杀了他。
何况祁煦和卫彰那两个心怀叵测的家伙还跟在先生身边。
祁尧并非没想过对姜卫两家下手,逼他们回来,但一来卫家满门忠烈,姜家如今虽无实权,也同样功勋卓着,无缘无故对他们动手,文武百官都会反对,二来,真要这样做,云子猗与他的关系只怕更要万劫不复。
他实在不敢。
甚至还要每日兢兢业业地处理朝政,照拂大齐的每一寸土地,不敢有丝毫懈怠,祁尧知道云子猗一直对自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一代明君,给天下百姓一片海晏河清,祁尧自不能辜负他的教导和期望。
只能在疲惫的深夜,蜷缩在他们曾做过无数次最亲密的事的床榻上,臆想着这里还残留着一点属于云子猗的气息,偷偷思念。
可他明明都已经这么乖了,先生怎么还不肯心疼他一点,原谅他一回,再见他一面呢?
哪怕是……梦里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