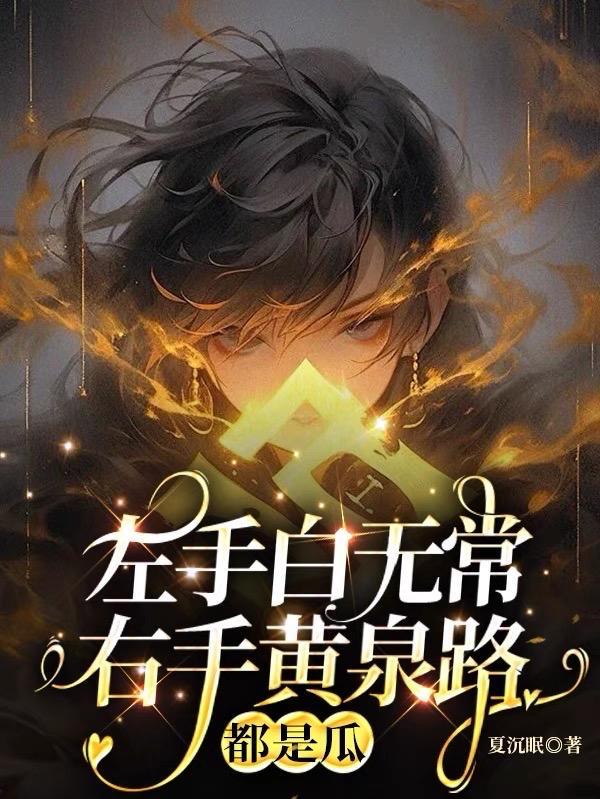九曲小说>我是首富的亲姑姑[年代文] > 29 第029章 拒绝(第2页)
29 第029章 拒绝(第2页)
面对她的苦口婆心,谢君峣却神情冷淡。
“我最讨厌有人打着为我好的名义做着对他自己有益的事情。”他语气冰凉,眼神也透出一股寒意,“我已经有喜欢的姑娘,我正在追求她,我不希望任何人任何事来搞破坏,请您立刻打电话通知张太太,别管什么张宝仪王宝仪,我都不会见。”
谢太太很不高兴:“哪家的小姐?怎么没听你说过?”
“我没瞒着您是因为我们光明正大,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您不用问她是谁,我不需要向您交代什么。”谢君峣站起身,目光下垂,落在谢太太保养极好的面孔上,“您就安安稳稳地做您的谢太太,这不是您一直以来的愿望吗?不要管我和大哥的事情。”
谢太太越发恼怒,跟着站起身,眼睛不自觉地红了。
旁边的女佣瞧见了,悄悄后退两步。
假装看不见,听不到。
但谢太太声音尖利,由不得做下人的控制,冲着谢君峣道:“我是你妈,我就不能挑自己喜欢的儿媳妇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告诉你,谢君峣,我的儿媳妇进谢家大门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我不许你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小妖精,做有损谢家颜面的事情!”
谢君峣冷冷地道:“谢家大门有什么好进的?很高贵吗?不稀罕!您不用担心,我和大哥都不住在谢家,她自然不进谢家的大门。”
说完又道:“您的意愿不重要,我不希望下次听您口出恶语,毕竟恶语伤人六月寒。”
“你……”谢太太被气得呼吸急促,一个劲地捶着胸口。
捶着胸口的右手手指上戴着三枚戒指,中指戴着碧绿的翡翠指环,无名指戴着硕大的钻石戒指,食指戴着红宝石戒指,光泽灿烂,极是绚丽。
谢君峣指挥女佣过去帮忙,自己却不上前。
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仿佛一尊玉雕,没有半分人气。
女佣的动作相当熟练,轻巧而又有效。
谢太太顺过气,见威胁不成,马上示弱,哀伤地说:“君峣,你真的要气死我吗?做儿子的怎能违逆为娘的命令呢?你年轻,不懂外面那些小妖精攀龙附凤的心思和花招,容易被她们迷惑,你要快快清醒,去见我给你挑的名门闺秀。”
“您请回。”谢君峣直截了当地道。
他对女佣说:“送太太上车,麻烦司机转告老爷,如果太太再来打扰我的生活,我不介意跟大哥说,让大哥把他们下个月的生活费砍一半。”
女佣低头应是,伸手去扶谢太太,“太太,请。”
谢太太顿时涨红了脸,甩开女佣的手,嘶吼道:“谢君峣!”
谢君峣淡淡地道:“因为您和父亲生养我和大哥,所以我们奉养你们、孝敬你们,但你们不应该倚仗父母身份来命令我们、控制我们。既然这么多年以来都在外人面前维持家庭和睦的体面,请你们继续保持下去,对大家都好。我正在追求我喜欢的姑娘,若是让我知道谢家有谁在背后乱搞小动作,我不介意大义灭亲。”
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凛然的神色,掩不住一丝丝杀意,和谢太太进门时见到的温柔青年简直是判若两人。
谢太太不敢挑战儿子的耐性,只能气呼呼地离开。
谢君峣坐到沙发上,脸上露出疲惫神色。
生在一个畸形的家庭里是一种悲哀。
父亲谢成功风流成性,处处拈花惹草,偏喜欢在外面装作正人君子,诱惑无数年轻女子奋不顾身地扑过来,有些被他纳做妾室,有些却被他始乱终弃。
母亲在外人面前优雅从容,不失风度,在丈夫跟前温柔顺从,处处以夫为天,在公婆面前孝顺有加,做足儿媳妇的本分,甚至在妾室跟前亦颇有主母风范,唯独在儿子面前像一个疯子,动不动就发怒,对儿子非打即骂。
她欺负的只有一个谢君峣。
因为谢成功不靠谱,谢君峣的大哥谢君颢从小便在祖父母身边长大,受其教养,谢太太轻易碰不到他,也有可能是那时候她病得不严重。
谢君峣出生得晚,是谢太太为了挽回丈夫才又生下来的,当时她已有三十四岁。
可能是病得很严重了,她在外人、丈夫、公婆面前表现得越好,在儿子面前发疯得越厉害,谢君峣从生下来长到三岁,身上就没一块好皮肉,全藏在衣服底下,谢太太对外面说她亲自照顾儿子,从不假手他人,也不叫别人抱他,每次都避开所有人在屋里又打又骂,有一回差点把他给掐死,幸好被回来看望弟弟的谢君颢及时发现并出手阻止。
谢君颢送她去国外治疗过,说是心理上的疾病,但治疗效果不大。
后来,谢君颢直接把弟弟挪到自己院中,让心腹照顾,不让谢太太接近,从上海搬到香江,先在两处唐楼暂住,再买两块地皮盖新屋,一处在山顶,一处在是山腰,分开住。
谢君颢没有结婚,他把弟弟当儿子一样抚养,总认为是他疏忽导致弟弟受那么大的罪。
谢君峣从没怪过自己的哥哥,他十六岁出国读书,四年后学成归来,从祖父手里接过家里的生意,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自然不可能发现母亲的异常。
谁能想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