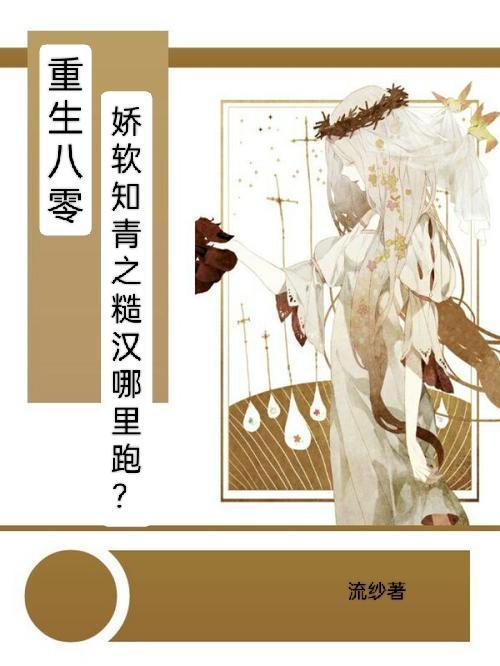九曲小说>我所知道的铁道游击队 > 第54章 屈辱苟活(第1页)
第54章 屈辱苟活(第1页)
张允骥今年四十五岁,此时的他正在沙沟火车站的调度室里一个人喝闷酒,他咬牙切齿地喝下一盅酒,看到调度室墙壁上挂的那把东洋刀,“嚯”地站起身来,一把拽下,“刷”抽出钢刀,朝天虚劈一刀,嘴里叫道:“砍死你个龟孙!”
随后将刀一扔,无力地坐回椅子上,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沙沟是临城南边十几里的一个小站,即使每天日军的铁甲车“轰轰”地来回跑,这里也未引起重视,只有张允骥和两个巡道的工人,他的小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安逸的,几年前,他的前妻去世,经人介绍,又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老婆,每次在床上心满意足地忙活完,看着浑身瘫软的小娇妻,他都感觉自己的人生又一次走向了巅峰。
可是好景不长,他的噩梦来了。
一年前,临城的高岗觉得沙沟这个地方游击队比较活跃,没有人盯着容易出事,于是派一个叫福田的鬼子来这里当站长,将张允骥降为副站长,开始的时候,福田还是比较客气,每天只是盯着沙沟车站的调度室,观察车站附近的动静,其余的活由张允骥来干。
张允骥本就是逆来顺受的性格,他更卖力地干活,将沙沟的事情处理的井井有条。为了与福田处好关系,去年过年的时候,专门请福田到他家吃年夜饭。
这一下可是引狼入室了,福田看到张允骥的老婆,眼珠子都差点掉了出来,沙沟这个小地方,连个妓院都没有,早已把他憋坏了,突然看到这么漂亮的肥肉,岂有放过之理,当即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张允骥的巴结,心里却盘算着怎么对这块肥肉下手。
这顿年饭吃得自然是索然无味,张允骥又不傻,怎么能看不出福田的德性,好在福田也没有说过份的话,他便只能陪笑着勉强吃完饭,送福田回住处了事。
大年初三,本是拜祭灶王爷的日子,张允骥早早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福田突然告诉他有紧急任务,要他在车站值夜班,他不敢拒绝,枯坐在调度室里到半夜,突然想到,要给媳妇说一声晚上得值夜班,提醒她要关好门户,不要给他留门了。
他家就在车站边上,转弯就到,当他走到大门口的时候,看到大门洞开着,他有些紧张,赶紧快步走进院子,隐隐约约听到屋里传出来“嗯嗯啊啊”的声音,他登时感觉天旋地转,耳朵“嗡嗡”作响,心头怒火上窜,他拿起门边的铁锨,准备马上进去铲死屋里的这对狗男女。
左手搭上门的时候,他犹豫了,拿锨的手也抖了起来,探头悄悄从门缝里看去,他年轻貌美的老婆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赤身裸体的福田正死死地压在她身上,左手掐着女人白嫩的脖子,右手却握着乌黑的手枪。
张允骥两腿软,他知道如果现在进去,马上就要家破人亡,他的孩子还有住在古井的老爹就再也无依靠了。他眼前闪着光怪6离的景象,哆哆嗦嗦地放下铁锨,连大门也没有关,大脑一片空白地回了调度室。
他的心彷佛被刺刀捅了五七八个窟窿,嘴里一股腥味传来,扶着门框吐了起来,然而呕了半天,吐出的都是带血的泡沫。
一夜无眠,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女人,在大门口站了很久,门口树上那个老鸹窝里,老鸹“呱呱”地叫,似乎也在嘲笑他的软弱和无能。
他狠狠心,走进了院子,屋里很安静。他突然担心起来,快步小跑到堂屋门口,心里既害怕看到可怕的场景,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推堂屋的门。却听到屋里传来痛苦的哭声。
他停下脚步,心头怒火又起,伴随着屈辱感直冲脑门,魂不守舍地在门口站了半天,当屋里的女人哭声转成了抽泣,他头晕目眩的感觉也消退了一些,这才哆哆嗦嗦地推开堂屋门,跨过门槛,走了进去。
他年轻的老婆衣衫不整地缩在墙角,双手抱着膝盖,头散乱,两眼空洞无神,她或许觉得自己再也无法面对自己的男人了,一脸漠然地等待男人的审判。
张允骥在堂屋里又站了半天,看到女人痛苦的样子,愁肠百转,难过地走上前去,一把抱住自己的女人,抚着她一头乌,泪水涟涟。
从在大门外徘徊到走进屋子,他感觉彷佛过了一百年那样长,他已明白,这不是他的错,这也不是她的错,在这黑暗的年代,他和她都是可怜人,两个可怜人,谁又能抱怨谁呢?
就这样,暗无天日地过了大半年,福田隔三岔五地安排张允骥值夜班,值班的时候,他眼前总是不由自主会浮现出福田那强壮的身体压在他老婆身上的情景,他咬着牙忍耐着,以前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从来不喝酒,现在只能借酒消愁,值夜班的时候,长夜难熬,慢慢的酒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便抽上了大烟,他花大价钱买了全套抽大烟的工具,空下来的时候就抽上几口,只有吸上鸦片,他的身心才能全部放松下来,才能鼓起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但是,鸦片这个东西,沾上了就越陷越深,花费也越来越高,渐渐的,他那点收入加上福田偶尔给的安慰钱已经支撑不住。他就天天想着找周围的人问门路去赚外快。
小雪已经过去了六天了,天气也越来越冷,张允骥盘算着,家里的煤球还需要补一些,下个月的鸦片钱还没有着落,正在调度室想着怎么弄钱。有人过来送给他一封信,信是多年前夏镇的朋友张运海(张新华)写的,说介绍个姓王的老板给他做笔生意。要他一个时辰后到沙沟东边的合成酒店会面。
张允骥知道张运海可能是游击队,但是,夏镇离沙沟不远不近,和这边的鬼子也没什么瓜葛,加上他求财心切,便收拾了一下,穿上大棉袄,戴上狗皮帽子,抄着手径直去了合成酒店。
酒店里冷冷清清的,屋里生着炉子,稍微暖和些,张允骥进了门,摘下帽子习惯性地拍了拍,一个酒保过来招呼道:“张站长来了!到雅座吧,王掌柜已经到了。”
这时,一个大四方脸,从雅间悠闲地走了出来,边招呼边自我介绍道:“张站长,我叫王强,是夏镇的张大掌柜介绍来的。”
张允骥也没做过生意,又不想露怯,就装模做样地拱手说道:“王掌柜,运海是我多年的老兄弟,他的朋友来了,我理应招待好,正好今天站上没事,过来请你喝两杯,不过这兵荒马乱的,你们要做什么生意?”
那王强哈哈一笑:“边喝边说吧!”
进了雅间,里面还有两个人,都是短,眼神凌厉,一看就不好惹,张允骥不禁心慌,心道这个王强还带两个保镖,要么是做大生意的,要么就是山里下来的马子,不会是来绑票的吧,他不禁心提到了嗓子眼。
那王强看他有些紧张,便拍拍他的肩说道:“这两个是自己兄弟,他姓徐,他姓孟,张站长不用担心。我呢,准备做点布匹生意,由于铁路上咱不熟,有布运不出去,走旱路又不方便,到处是卡子,每个地方上点供,连利都赚不出来。这个生意呢,不需要你出面,也不需要你出本钱,只需要你在铁路运输上提供点方便就行。”
张允骥看不是绑架他的,便放下了心,觉得这个买卖比较划算,当即来了兴致。
酒保已经将菜端上来,又上来一坛子高粱酒,对面姓孟的捧起坛子斟了四碗,分别摆好,四个人就喝了起来,酒酣耳热后,张允骥话多了起来。说起日本鬼子,咬牙切齿地骂站长福田是个畜生,王强面带愤怒地附和着,张允骥觉得生意有谱,似乎生活又看到了希望,便慢慢放开了,不断与徐孟二人碰杯。
喝到最后,张允骥说:“做生意咱就按做生意的规矩来吧,咱们订个协议,签上字,毕竟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王掌柜你看行吗?”
那王强支支吾吾地说道:“那是,那是,咱今天没想到能谈这么顺利,没有写好协议,你看明天我带着协议到车站找你,怎么样?”
张允骥想了一下:“这个事毕竟以后要走铁路线,不能让日本鬼子知觉,车站不是很方便,俺在乔庙还有个住处,咱到那里签比较安全。”
三人对视一眼,当即同意了张允骥的建议。